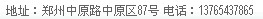|
白癜风最快治疗方法 https://m-mip.39.net/woman/mipso_6329464.html点击“蓝色字” 刘奕,中国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席专家、临床著名专家。现任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医院正畸教研室和正畸二科主任。兼任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从事口腔正畸医疗、教学、科研工作32年。主要研究方向为高发错牙合畸形的早期干预治疗、疑难错牙合畸形的正畸治疗、临床罕见病的诊疗、牙周膜干细胞外泌体复合水凝胶促进骨缺损修复的研究、口腔生物材料关键技术研发等。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16项。发表学术论文篇,其中SCI收录35篇。主编专著2部。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10项。 作者姓名:岳杨,刘奕 基金项目: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JH2/);沈阳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20--4-) 作者单位: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医院正畸教研室,辽宁省口腔疾病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通信作者:刘奕,电子信箱:liuyi cmu.edu.cn摘要:外泌体是细胞外囊泡中最小的一组,含有丰富的来自母细胞的信息,作为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细胞间通信和信号转导来诱发病理过程。近年来研究发现,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免疫调节、治疗等大部分过程。外泌体广泛存在于血液、唾液等体液中,对外泌体内容物进行检测分析,将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价和预后判断。文章就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的生物功能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做一阐述,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外泌体;肿瘤;口腔鳞状细胞癌;肿瘤微环境 口腔颌面部肿瘤是头颈部肿瘤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较高,其中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被认为是世界第六大常见癌症,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全球每年新诊断的OSCC病例超过60万[1]。OSCC具有发病隐匿、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易复发等特点,且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随着相关研究及临床技术的不断发展,OSCC患者治愈率有所提升,但患者预后仍然较差[2]。因此,寻找肿瘤诊断标志物及制定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外泌体作为一种细胞外微小囊泡,可通过转运其亲代细胞的活性物质至受体细胞发挥调控作用[3]。近年来,在肿瘤学领域中,外泌体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成为新热点,已有研究表明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等生物过程,在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中可能具有应用价值[4]。因此,本文就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的生物功能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做一阐述,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的生物学功能 1.1 介导肿瘤的恶性进展 肿瘤细胞通过与自身微环境进行信息交流来促进其增殖,而外泌体是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肿瘤细胞有选择性地将生物分子装载到外泌体中并释放,可能在肿瘤的恶性进展中起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Dickman等[5]研究发现,OSCC通过选择性地将miR--3p装载到外泌体中,并运送至周围肿瘤细胞和其他细胞,激活相关信号通路,进而影响肿瘤细胞的活性。此外,Sakha等[6]研究还发现,高侵袭性的口腔癌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装载特定的微小RNA(miRNA),如miR--3p和miR-等,转运到周围低侵袭性癌细胞中,通过激活ERK和AKT信号通路,从而增强周围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巨噬细胞的浸润和极化在肿瘤癌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Xiao等[7]研究发现,巨噬细胞在早期通过p38、Akt和SAPK/JNK信号通路,摄取OSCC来源外泌体而被激活;进一步研究表明,OSCC来源外泌体中的血小板反应蛋白1(THBS1)参与了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的过程,并显著促进OSCC细胞的迁移。 缺氧是实体肿瘤的一个常见特征,与肿瘤侵袭性强及患者预后差有关。对正常和缺氧条件下OSCC来源外泌体进行miRNA测序显示,低氧条件下改变最显著的miRNA是miR-21。这提示缺氧微环境可能会刺激口腔颌面部肿瘤细胞产生富含miR-21的外泌体,并将其递送至含氧量正常的肿瘤细胞中,通过激活乏氧诱导因子HIF-1α和HIF-2α,促进含氧量正常的肿瘤细胞发生迁移[8]。? 1.2 参与肿瘤免疫反应 在口腔颌面部肿瘤的各种免疫抑制机制中,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配体(PD-1/PD-L1)信号通路是目前研究的热点[9]。Theodoraki等[10]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患者血浆中发现了携带PD-L1和抑制T细胞功能的外泌体,并证明外泌体中PD-L1的含量与患者疾病的发展、淋巴结转移状况及UICC分期有关。Razzo等[11]从HNSCC细胞系的上清液中分离了携带PD-L1和人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asL)的外泌体,将其注射给具有免疫原性的C57BL/6小鼠[该小鼠由致癌物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诱导发生口腔和食道癌变];单次注射后,小鼠体内肿瘤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加,同时发现CD4+和CD8+T淋巴细胞的数量受到抑制,呈协调性降低。 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不仅能够抑制免疫细胞,也可增强相关免疫细胞的活性,如增强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的表达及其磷酸化,促进Ⅰ型干扰素(IFN)和趋化因子配体(CXCL)的表达,从而促进了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性[12]。 1.3 参与肿瘤血管生成 外泌体能将携带的自身细胞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管生长素等)释放到细胞外,作用于内皮细胞膜表面受体,促进血管形成,进而加速肿瘤的生长[13]。Yang等[14]研究发现,腺样囊性癌(SACC)细胞中上皮调节蛋白(epiregulin)的表达上调,并通过调节GLI1/E-cadherin信号通路,来诱导上皮-间充质转化,增加促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bFGF和IL-8等)的表达。上皮调节蛋白可以通过外泌体递送到肿瘤微环境中,体外实验显示,其不但可以增强肿瘤微环境的血管形成,而且可以增强肿瘤细胞肺转移前微环境中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 Sonichedgehog(Shh)信号通路对于胚胎发育、细胞分化和血管生成至关重要,其异常激活已在多种肿瘤中被发现[15]。Huaitong等[16]研究显示,OSCC来源外泌体中表达Shh信号通路中的Shh与GLI1,且在转移的淋巴结来源外泌体中,Shh与GLI1的表达水平更高;并在体外实验中发现,OSCC来源外泌体能够增强内皮细胞的血管生成能力。 1.4 介导肿瘤放化疗耐受 口腔颌面部肿瘤的治疗虽然一直是以手术为主,但放化疗也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临床上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发生耐受[17]。研究发现,在同一肿瘤微环境内,耐药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作用于周围敏感细胞,促使其产生耐药表型[18]。此外,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也可以直接包裹药物,介导药物外排[19]。Yoshikawa等[20]研究显示,对抗癌药物顺铂耐受的OSCC细胞分泌的外泌体,携带大量的P-糖蛋白(P-gp),而P-gp是肿瘤细胞多药耐药基因MDR1的表达产物,被周围细胞摄入后,P-gp能够与抗癌药物顺铂进行结合,并将顺铂从细胞内泵出细胞外,从而降低细胞内的药物浓度,促使肿瘤细胞产生耐药性。目前,肿瘤细胞生长及耐药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外泌体可能成为治疗肿瘤细胞耐药的潜在靶点。 放疗是OSCC晚期及不能手术完全切除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外泌体在急性辐射应激反应中参与肿瘤细胞间的信号传递,辐射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进入周围肿瘤细胞后,外泌体中的miRNA能帮助修复其他肿瘤细胞内断裂的DNA双链,从而增强肿瘤细胞对放疗的耐受能力[21]。一些情况下,放疗也可能会促进口腔颌面部肿瘤的侵袭和转移。Mutschelknaus等[22]研究显示,经放疗后的OSCC来源外泌体,可以促进OSCC细胞的迁移。这可能是由于辐射后的外泌体激活了AKT信号通路,促进了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和核糖体蛋白s6(rpS6)的磷酸化,并增加了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和MMP-9的活性。因此,改善放疗策略,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值得深入研究。 2 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在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中的应用价值 ? 目前,诊断口腔颌面部肿瘤及癌前病变的主要方法是术前及术中组织病理活检,但组织病理学诊断也无法完全识别可能发展为恶性肿瘤的病变,即很难做到早期诊断,有可能延误治疗时机,严重者影响治疗效果[23]。因此,临床需要一种快速、定量和经济的分子检测方法,以辅助组织病理学诊断。在许多恶性肿瘤中,分子改变往往先于表型改变,识别与恶性肿瘤发生早期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是早期诊断的关键。 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作为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丰富的肿瘤信息,且可广泛分布于各种体液中,如唾液、血液、尿液等,有望成为肿瘤早期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估的新型生物标志物[24]。Zlotogorski-Hurvitz等[25]研究发现,OSCC患者唾液中外泌体在形态和分子结构上与健康人群不同,OSCC来源外泌体中四跨膜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健康人群存在明显差异,CD81和CD9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而CD63的表达水平上升,提示这种差异表达的外泌体蛋白可能作为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此外,循环外泌体检测有望成为一种无创的肿瘤早期诊断方法。研究发现,OSCC患者循环外泌体中的circ_高表达,且与肿瘤大小、淋巴转移和TNM分期显著相关,高表达的circ_能够促进OSCC细胞生长,提示循环外泌体中的circ_可作为OSCC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26]。 除了早期诊断外,精确的预后判断也同样重要。但肿瘤患者的预后判断,特别是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判断仍是医学面临的巨大挑战。近些年,学者们开始对外泌体进行检测,以辅助肿瘤分型及预后判断[3]。Manikandan等[27]检测OSCC来源外泌体中miRNA的表达情况发现,miR-29b、miR--3p、miR-、miR-及miR-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表达的miR-与晚期肿瘤分期和肿瘤大小相关,而高表达的miR-与局部淋巴结浸润相关。RodríguezZorrilla等[28]研究发现,OSCC来源外泌体中CD63和小窝蛋白-1(CAV-1)表达水平低的患者,预后较好。而Siow等[29]研究显示,在OSCC早期和无淋巴结转移的OSCC来源外泌体中,miR-31的表达显著升高;在OSCC晚期、较大肿瘤和强侵袭性的OSCC来源外泌体中,miR-的表达降低。综上,随着研究不断地扩展与深入,以及综合检测多种生物标志物,外泌体检测有望成为口腔颌面部肿瘤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的重要方法。 3 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口腔颌面部肿瘤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手术治疗,其会对患者的吞咽、语言功能及外貌造成严重影响,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辅助治疗手段放化疗的不良反应较多,也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目前,口腔肿瘤免疫治疗是比较理想的新治疗方法,而外泌体则被认为是治疗和预防多种疾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是研究的热点。 Li等[30]通过在γδT细胞中过表达miR-,获取富含miR-的γδT细胞来源外泌体(γδTDE),γδTDE具有γδT细胞的细胞毒性特征,对T细胞具有刺激作用,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同时γδTDE可以有效地将miR-传递给OSCC细胞,靶向CD8+T细胞中的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增加CD8+T细胞的细胞毒性,起到抗肿瘤的作用;此外,γδTDE和miR-可以促进干扰素-γ(IFN-γ)的产生,从而对OSCC细胞起到协同抑制作用。 因外泌体参与OSCC的侵袭和转移过程,故靶向阻断外泌体的摄取途径可能有效治疗OSCC。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HSPGs)是肿瘤细胞来源外泌体受体,而肝素可以有效抑制HSPGs摄取外泌体,从而抑制肿瘤发展[31]。此外,靶向管理外泌体极化M1型巨噬细胞,在控制OSCC细胞迁移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7]。 外泌体也是理想的纳米药物载体,与其他载体相比,其免疫原性低、稳定性高,且有更强的渗透滞留效应。外泌体与靶细胞的受体-配体高效率结合,有助于药物的远距离运输及靶向给药等[32]。可以作为药物载体的外泌体已从多种类型细胞中分离出来,包括HEK-细胞、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癌细胞等;可以携带的药物类型包括蛋白质、小干扰RNA(siRNA)和miRNA等;药物可以通过电穿孔、化学转染、修饰亲代细胞或直接孵育等方式进入外泌体中[33]。Wang等[34]利用转基因技术修饰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过表达miR-,用其治疗由二甲基苯并蒽(DMBA)诱导的口腔潜在恶性病变(OPMD)鼠模型,发现OPMD组织中炎症严重程度显著降低,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得到抑制,延缓了OPMD的发展进程。 4 小结与展望 外泌体是细胞经一系列调控过程产生的纳米级微囊泡,其携带多种重要的信息物质。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参与调节肿瘤微环境及细胞间通信,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免疫逃逸、血管新生等过程。通过修饰或去除外泌体标志物,在口腔颌面部肿瘤治疗方面可能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外泌体可以作为OSCC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具有精度高、创伤小等特点[33]。然而,将其应用于临床仍存在许多难题,如从细胞系或体液(如唾液和血液)中分离外泌体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这就可能需要开发新的纳米颗粒分离/检测技术及设备;此外,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的可追溯性方面也存在问题,即肿瘤的位置可能无法被准确定位,此时靶向治疗就比较困难[35];而且,外泌体载药存在基因工程周期长、技术复杂、成本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达到高效负载药物的目的[36]。 综上,口腔颌面部肿瘤来源外泌体在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仍需要大量研究证明其临床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对于肿瘤的发病机制及外泌体的认识必将更加深入,利用外泌体构建口腔颌面部肿瘤诊疗体系,将是今后努力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 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kcme.com/mbyyy/134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