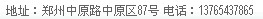|
这个场景至今让很多人记挂在心,说起他依然眼里噙满泪水。 那是年5月的一个早晨,初夏的重庆医院家属区花木葱茏,阳光下的绿树盆栽一派盎然生机。咫尺之外的门诊楼内外人声鼎沸,新的一天就这样循回往复,如常开始。此时一位耄耋老人,发白如银,慈眉善目,精神矍铄,正在一行人陪伴下缓缓走向一辆轿车。车门开启,老人躬身欲入,忽然间,他回身环视眼前的高楼庭院,眉宇间有多少不舍和挂牵……良久,从他的喉咙里嘣出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声音:“重医,我的重医,我走了!”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的麻醉学专家、重庆医院麻醉科原主任董绍贤教授。老人此时九秩高寿,应其子女董景辰、董景敏要求将他和夫人景用仪接往故地上海,安度晚年。 麻醉学,对于世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可是对于每一位动过大小手术的人,哪怕某一次注射,某一次拔牙,某一次内外伤患,你也就和它搭上了关系,从而成为就医、手术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成为人类生命保障的必备手段。 笔者和读者诸君一样对麻醉学几乎一无所知,一样对之有着特殊的神秘感,那就让我们随着董绍贤教授的生命脚步,去窥探它的神奇与伟大吧! 寻寻觅觅,认定医学可救国民于水火 和王鸣岐先生以及许多上医过来的同事一样,董绍贤也是浙江人。他生于慈溪,在老家读完初中方才去上海求学。青年人去大上海发展才有出息,这几乎是当年浙江工商地主官宦人家子弟的必由之路。上海是世界有名的远东大都市,十里洋场,经济发达,教育环境、思想观念以及师资设施自然大大超越浙江,就业前景也远非杭州宁波能及。可是董绍贤在上海读完三年高中,并未像一般有钱人家子弟一样继续深造,而是报考了当时颇为时兴的无线电培训班,结业后在南京当了一名半军事化的收发报员。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无线电报务员可算个时髦的职业,可是董绍贤没兴趣。那些数字和密码对于他太虚幻莫测,他常常在工作之余神思遐想,一心寻找他以为于国于民有益,自己又深深热爱的工作。年9.18事变,日本人全面占领东北,此后大批流亡人士入关逃往沪宁一带,也有伤兵病民滞留街头路边,年及弱冠的他每每碰见,都会从自己微薄的薪酬里拿出一些,救济这些苦难的同胞。饥民灾民嗷嗷待哺病入膏肓,此时就有打着红十字会标的救济人员医务人员出现,让面善心慈的董绍贤心底也泛起温暖。有一天,他忽然幡然醒悟:不干这报务员了,我还年轻,我学医去,救百姓于水火,去东亚病夫之臭名,终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实实在在急需的事。 决心已定,立马辞职,立马行动,立马温习已经丢弃了几年的高中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夏天,21岁的董绍贤成功考入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医学学府---国立上海医学院六年制本科,主修临床儿科学。此后学业和工作可谓一帆风顺。年毕业后,医院工作,任医师、主治医师;医院,任儿内科副主任;年进入上海美高德士古石油公司,任中国职工保健医师。大学期间,他结识了正在某教会学校读书的大一女生景用仪,不久后遂结为连理,相许终身。景用仪乃来自武汉的大家闺秀,英文特好,两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她从此放弃了学业,追随了董绍贤先生一世一生。 改行麻醉,为创立发展现代麻醉学呕心沥血 时下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恐怖可怕的镜头:医院因为没有麻药使用,往往用点酒精一涂,拿把木锯就开始截肢,拿个刀片就开始破腹割肉;为抑制疼痛,让伤员嘴里咬着毛巾,头上大汗淋漓直至昏厥过去……其实即便在当年的大城市上海,麻醉技术也停留在很落后的水平,无论是器械还是技术;更没有科学的论述和临床的权威实践。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西方诸国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致使我国的麻醉学研究形同空白。 所幸此时从美国回来了一位麻醉学专家吴珏。 年初,吴珏教授留美归国。和那个时代许多学成归来的莘莘学子一样,他们是满怀报国之心回来的,因为他们看见了新中国如冉冉升起的朝阳,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有,百废待兴,他们回来是要建设这个伟大的国家,让祖国重回世界强国之林。吴珏立志振兴中国的麻醉学,可是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设备和药物,更没有人才。吴珏先生和董绍贤先生都已作古,笔者已无从了解到吴珏当年是怎样看上董绍贤的。但是在所存无几的资料里,我看到董绍贤先生的一份自我“专业技术工作述评”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推荐我返回母校,协助其完成这一理想。” 其时董绍贤已经从事了十年儿科临床医疗工作,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后又在上海美高德士古公司任职工保健医师,可谓名利地位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去从事自己不熟悉的麻醉学研究呢?兴许是因为吴珏教授精神的感召,也许因为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帝国主义列强不是封锁我们么?我们买不到高效麻醉药,更买不到先进的设备,致使外科许多大型的和较为复杂的手术都无法开展。中国人从来是不怕威胁封锁的,如此只能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自找门路了。 吴珏教授是有心人。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册美英麻醉学杂志,成了董绍贤他们最好的教材;他在美国学到的麻醉学知识、麻醉学临床实践,以及使用的麻醉药物和器械等等,都成了他的学生们、同事们共同的财富。他们日夜研读,分析推演,反复论证,深思熟虑,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决定把硬膜外麻醉术作为首个主攻对象,同时在上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麻醉学教研室,由吴珏担任主任,董绍贤任副主任。 有了队伍也有了目标,他们开始尝试制造麻醉工具,并且协助相关药厂研制高效麻醉药,在各类手术中推广使用。经过整整8年的艰苦探索,反复总结,不断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开发出一套高效安全、费用低廉、适用于腹部以下各类大小手术的“硬膜外麻醉术”。成功得来实在不易,近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可谓殚精竭虑,注重临床实践,注重每一个细节,注重理论提升,使之愈加成熟简练,成为国内麻醉学研究的经典技术。8年中,先后有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山西、新疆、武汉等省(自治区)市医学院校派员前来学习取经,他们后来都成了我国早期麻醉学骨干人才。这支20多人的麻醉学骨干回到当地以后,又将他们学到的专业技医院推广普及,有如滚雪球般日积月累,繁衍生息,据粗略统计,至上世纪末,国内80%医院都已经备有专职麻醉师使用这一优秀麻醉技术,从而凸显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年,就在他潜心研究麻醉学的时候,董绍贤受命调往上医院任麻醉科主任、副教授。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在国内首创并推广了硬膜外阻滞麻醉技术及相应的器械,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陶根记”麻醉机,同时改良了气管插管套囊技术,使我国在西方国家的药品和技术封锁的艰苦条件下仍能开展各种常见手术的麻醉。董绍贤教授还改良了骶管阻滞麻醉技术、颈丛神经阻滞技术、半开放式麻醉技术,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后颅窝坐位手术麻醉。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倡导世界性项目——无痛分娩的研究和开展。董绍贤教授的一生填补了我国麻醉学专业的许多空白。 四年之后的年10月,他奉命支援内地,前往甫建不久的重医院组建麻醉科,并担任相应职务。 援建重医,在荒山僻岭上描画新图 我本不想重复评介援建重医的每一位专家的心路历程,但是董绍贤教授的表现还得写一写。用他的钢琴家女儿董景敏的话说,父亲是一个心胸宽敞的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真正是忧国忧民不计得失,对组织的决定是言听计从,上边定了的事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出发。家里完全没得商量,他听组织的,母亲景用仪听他的,弟弟董景辰年纪小自然也得听他的。只有她正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重庆没有相应的学校可去,所以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人是把能去艰苦的地方工作引以为荣的,国家的需要就是一切。 所有来到重医的上医专家面对的困难几乎都是一样的,穷乡僻壤,泥屋茅舍,交通不便,有点思乡。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医疗教学设备匮乏,难以正常开展工作。新成立的重医附一院麻醉科更是如此,一切都需白手起家。上海当时毕竟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医疗设备、人才储备、药物研制没有哪个国内城市可以与之相比。重庆就不好说了,抗战时期搬来的学校迁走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回去了,医疗设施之落后,器械物资之匮乏,令董绍贤一行大为吃惊。吃惊之后还得静下心来想办法。 随丈夫姚臻祥(外科教授)来渝的唐伟玲一直在董绍贤教授领导下工作,说起当年的人和事,白发苍苍的老人兴致勃勃。“当年那个条件呀,年轻人是不晓得的,真是要啥没得啥。从上海带过来的一只弹簧血压表都成了宝贝,如今都成文物了我还保存在身边呢!”她说,重医的麻醉学科,就是董教授亲自创建发展起来的,那时候重庆没人敢做胸外科手术,更没人敢做脑外科手术。董教授一来,不仅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思想,带来了手术麻醉的规范程序化,还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自制设备。帝国主义不是封锁我们嘛,他就带领我自己做,大到麻醉机,小至一针一管,都是自己设计制造,逐步摸索改进,为医院各科手术麻醉做了最充足最安全的保证。重医胸外科麻醉和脑外科麻醉,都是从董绍贤始! 麻醉科原主任李秀英说到老主任董绍贤更是如数家珍。她说在董教授领导下工作收获大进步快,天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年,她奉命参加援藏医疗队,那时她只是一个到院三年多的住院医生,可以说好多东西还没搞明白,可是去了拉萨就得独当一面。怎么办?那时候长途电话费贵,拉萨打到重庆尤其贵,一般人哪里承担得起?只能写信。即便信也要在路上走十天半月。每每有一点疑难问题她就写信向董主任请教,董主任可是见信必回,从不拉欠。两年下来,李秀英收到一大摞他的回信,学到了好多好多麻醉学知识,这是真正的医学“两地书”。她在麻醉学的医教实践中迅速成长,多年以后,已成为重医新一代的麻醉学专家。 虽也已退休,却显得非常精干的李秀英对我说,董绍贤教授一生可谓卓越不凡,教书育人、辛勤耕耘、动手动脑,永远走在创新的路上。在上世纪50—80年代,为推动重医附一院以及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麻醉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麻醉界的先驱。为证明她的判断正确,还从下面三个方向写了非常专业的说明,为保证准确无误,笔者只能抄录如下了: 1.对单次硬膜外麻醉穿刺针的引进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70—80%的外科手术采用局部麻醉,包括硬膜外间隙注射局部麻醉药(即硬膜外麻醉)和蛛网膜下间隙注射局麻药(即腰麻)。而硬膜外麻醉较腰麻发生头痛、尿潴留等并发症更多(少?—笔者注),麻醉可控性好,手术适应症更广泛,麻醉安全系数大大提高。由于那时硬膜外麻醉器械稀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硬膜外麻醉的广泛使用。董绍贤教授自己动手,将尖锐的腰麻穿刺针尖端磨成圆弧形,使其变钝成勺状。采用这种改良的腰麻穿刺针行硬膜外穿刺时可避免穿破硬脊膜而进入蛛网膜下间隙发生腰麻的并发症,即可安全的进行硬膜外麻醉,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2.早期创造性开展连续硬膜外麻醉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术范围扩大,疑难手术增多,除全身麻醉外,单次硬膜外麻醉已不能满足较长时间(大于两小时)手术的麻醉,需要改单次硬膜外麻醉为连续硬膜外麻醉。虽然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硬膜外穿刺针、可不能改良的腰麻穿刺针,然而连续硬膜外麻醉导管又买不到。董绍贤教授创造性应用普通的塑料细管(中间是空心的)经特殊消毒处理后行连续硬膜外麻醉获得成功,在以后的20多年一直沿用这种塑料管。直到90年代初麻醉器械的改进和标准化要求,才有了目前使用的带刻度的专用于连续硬膜外麻醉的导管。 3.创造性自制乙醚挥发罐解决全身麻醉急需设备某些外科手术要求在全身麻醉下进行。全身麻醉时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患者无意识,全身不感到疼痛。在上世纪60、70年代,麻醉器械稀缺,全身麻醉机更少。董绍贤教授自制乙醚麻醉挥发罐,将自制仿“亚利氏”麻醉机的三通开关安在挥发罐上,形成一个半开放的吸入麻醉方式。麻醉中患者保持自主呼吸,麻醉深浅可控性好,麻醉安全系数提高,麻醉后苏醒快,全身麻醉并发症降低。这在那样的年代,麻醉作为外科手术的幕后英雄,创造条件配合手术的需求,为外科手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麻醉就没有外科的发展,而外科手术的发展也促进了麻醉事业的蓬勃发展,董教授的创新也证明了这点。 现任麻醉科副主任的陈萍教授说起董绍贤先生也是眼含泪光,滔滔不绝。因为她也是董绍贤教授一手一脚带出来的。年,品学兼优的她从临床专业毕业,原本一心想去心内科,却被神经外科的杨维医生推荐给了董教授。可她对麻醉学了解甚少,正在犹豫之时,董教授找她谈了话,详细介绍了麻醉科的来龙去脉、发展前景,建议她不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临走还送给她好多《中华麻醉学》杂志。她说,那次谈话彻底改变了她的医学道路,从此与麻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萍那时很年轻,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幻想,但是当面对董教授这样的国内知名大学者大专家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和医学魅力立刻征服了我,我觉得应该去麻醉科,义无反顾!人生难得一知己足矣,她和董教授成了忘年交。30多年下来,她觉得这条路走对了。后来工作,读研,结婚,生子,升职,提干,可谓一帆风顺,如今也已成为麻醉学知名教授。无论做人还是做医生,她说,都得益于董教授的谆谆教导,没有他的教诲与提携,兴许我就没有今天的收获与成功。 知恩图报,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沿袭不弃的品德,如今正在李秀英、陈萍她们身上熠熠闪亮。我想董绍贤先生在天之灵有知,也会为弟子们的成就和感恩而欣慰不已。 陈萍真是有心人。除了李秀英教授前面列举的诸多医教科研临床成就,她还给我送来了几大页手写的董教授专业与学术的贡献详细资料,让我大为震撼,耳目一新。可我写的是非学术文章,不可能将之全文照录,还是摘其要点以豹见一斑吧! ——董绍贤教授和房秀生教授将硝普钠用于颅内动脉瘤夹闭的控制性降压……至今该药物一直在临床中使用; ——董绍贤教授和蒋夏教授将大剂量芬太尼麻醉用于体外循环心血管手术……至今也在麻醉界沿用; ——董绍贤教授率陈敦敏教授将传统颈丛神经阻滞方法改良为肌间沟注射法,应用于颈前部如甲状腺手术等……; ——分娩镇痛……董绍贤教授和陈敦敏教授尝试用硬膜外麻醉或者骶管阻滞来行分娩镇痛,意识超前; ——重新启用腰麻的准备……董绍贤教授曾经在准备好全麻的情况下,又在对传统的腰麻进行改革。可惜因退休未能继续。 ——将硬膜外麻醉成功用于肾移植受体的麻醉,为董绍贤、陈敦敏二位教授亲为,手术非常成功,乃重医附一院第一例肾移植手术。 …… 实际上,作为麻醉科现任主任的景苏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全面概括了董绍贤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医教建树—— 年10月董绍贤教授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从上海来到相对落后的重庆市,在艰苦的条件下参与创建重医院麻醉科,任麻醉科首届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全国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麻醉学专业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麻醉专业委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华麻醉学杂志》、《临床麻醉学杂志》、《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编委。董绍贤教授是四川省及重庆市麻醉学界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现代麻醉学的创立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年退休,载入重庆市卫生志。 董绍贤教授是建国以来最早投身麻醉学专业的人员之一,从事麻醉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40余年,对我国麻醉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董绍贤教授是重庆医学院第一位麻醉学硕士导师,培养了大批麻醉学专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人现已成为当今麻醉界的知名人士和学科带头人,如房秀生教授、张德仁教授、陈敦敏教授。~年他曾先后主持举办了四次重庆周边区、医院麻醉人员培训班,学员数百人,填补了这些地区的麻醉空白。 董绍贤教授以毕生的教育经验和体会为基础,综合参考国外麻醉学教材和论著,亲自编写了多部教材及著作,对创建我国特色麻醉学教育理念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重庆医学院医疗系麻醉学教材(主编)、《外科学-高等医药院校协作编写试用教材》(合编,书号-)、《外科学-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合编,书号-),《外科学-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合编--),《麻醉并发症》(主编,),《静脉麻醉药理及临床应用》(合编),《妇产科理论与实践》(合编),《难产与围产》(合编)。 董绍贤教授的主要科研及技术革新成果:后颅窝手术坐位麻醉()、硬膜外激素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神经痛()、乙醚麻醉半开放式装置()、食管异物取出的麻醉处理()、骶管阻滞改良途径()、芬太尼静脉麻醉(),这些技术革新成果均在院内外推广应用,受到一致好评。 董绍贤教授的代表论文: 一种改良的骶管麻醉方法。中华外科学杂志, 硬膜外麻醉用于分娩止痛20例。中华麻醉学杂志, 硝普钠用于控制低血压。中华麻醉学杂志, 硬膜外吗啡用于剖胸手术后止痛。中华外科学杂志, 麻醉技术的临床应用。中华麻醉学杂志, 足够了,这些文字和资料,已经给我们描绘出一位麻醉学大师的丰满的形像,让我窥见了董绍贤教授五彩斑斓的麻醉人生。惟有崇敬,惟有膜拜,惟有怀念。 亦师亦父,兢兢业业写出诗意人生 我曾几次电话联系远在上海北京的董景敏、董景辰姐弟俩,让他们谈谈父亲,谈谈他们和父亲的故事。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讲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更没有我所希望的细节和桥段。不怪他们,钢琴家董景敏年以后就和父母分居沪渝两地,难得见面,再次团聚已是45年后的年。高级工程师董景辰虽然跟随父母来重庆六中(今求精中学)上高中,但是每周才能回家一次,每次都要翻越高高的鹅岭,回到家也不一定能见到他,他的工作太忙了,成天都泡在科室里病房中,见了面也说不上几句话。他说虽然父亲当时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看不出和老百姓有啥不同,也没看见他买什么新衣服,最常见的就是一身白大褂。他自己常年住校,从未有过特殊照顾,此后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和父母也就地北天南,难得一见。他们说,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父亲母亲,他们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事业,献给了重医。 说实话,我听着电话那头冷静的叙述,心里头有几分心酸,我比他们小不了几岁,我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生活。我说,好吧,不麻烦你们了,你们的父母很优秀,你们也很优秀,这就足够了,起码他们给了你们非凡的遗传基因。我的话让他们轻松了许多,反过来安慰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麻烦你了哟! 恰恰相反,董教授麻醉科的老部下和弟子们说起老领导却热情不减,抢着发言。这个说,董教授待我们如子女,百问不厌,有问即答;那个说,为了帮助我们提高英语水平,每周星期二下午是固定的学英语时间,长期坚持不懈,学的都是英语医学原著或者期刊选段。这对提高科室人员英语实用水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董教授退休了,蒋教授又接过来,至今业务学习仍然在周二下午,形成了几十年不变的好传统。 对于青年医教人员的培养,董绍贤一向抓得很紧,新教师上大课前都必须在科室试讲,让大家来挑毛病,改正了通过了才能上讲台。无论新生老手,他都要拣过拿错,哪怕一次板书,一个手势,都要给你示范纠正,更不用说你的教案和讲稿了。他带出来的研究生,个个品学皆优,无论在院内院外都出类拔萃,成就斐然。其中有位硕士研究生张德仁,毕业答辩时,远道而来的考官、医院金士翱教授夸他已经达到了博士生水平,如今的张德仁医院的麻醉学专家。 年就到麻醉科做护士的张幼君说起老教授感慨万千。科里每周有一次大扫除,要用水冲洗地板,作为泰斗级的老专家,年事已高,本无他事,可是他每次都全副武装穿上水靴亲自干,谁也劝不走他,谁劝还和谁急。早年条件艰苦,没有空调,冬日里他每天早晨都要赶来科里提前生好火炉,烧水控温。夏天重庆持续高温,他们只能搬来冰块降温。董教授从来没有架子,大小事情都要身体力行。她说,即便文革中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下了台,罚他每天打扫厕所,他也无怨无悔一丝不苟,天天守在那里,扫的厕所也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绝对没有尿骚味。 后来他从科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不让他上手术台了,他依旧闲不住,每天在手术室里挨个巡查,他可真是火眼金睛,但凡不规范的操作大老远就看出来了。有一次一个8岁小女孩做扁桃体手术,做的半开放麻醉,中途麻醉师发现病员缺氧,发生紫绀全身肿胀,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手足无措时他正好在巡视中,立马前往处理,掀开手术单,发现氧气管滑落在口腔,病员已经极度缺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直到他75岁正式退休,几十年中,他把科室和手术室当成了自己的家。 科室的同志们都说,他是严师,更像慈父。业务上他是绝对的严师,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懈怠;生活上工作上他是真正的慈父,他有困难不会告诉你,你有困难他绝对会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件事让陈萍至今仍感念不忘。有一年董教授做了两次小手术,他的孩子不在身边,科里就安排年轻医护人员去他家轮流陪护。陈萍其时已有三个多月身孕,董教授知道后坚决不要她去陪护,说孩子比我这个老头子重要,你回去吧回去吧,态度绝决得不用置疑。 坐在我面前的唐伟玲、宋剑云、陈玉洁、易凤琼、唐万碧、罗小庆、米智慧、张幼君……以及前文提到的李文秀、景苏、陈萍,居然没有一位是男丁?我想,兴许女人心细,女人恬静,她们才会聚集到董教授的麾下,组成了强大的娘子军,帮助他塑造了堪称完美的麻醉人生。 其实生活中的董绍贤教授爱好广泛,充满诗意。他喜欢读书,喜欢写毛笔字,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文青,据说当年他乘船溯江而上经过赤壁时,被浩瀚奔腾的长江所感染,曾经高声朗诵大诗人苏轼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他还拉得一手好京胡,会唱小半场京剧《洛神》。每每假日佳节,他也会买来火锅底料,毛肚鸭肠,与科里老中青三代来一场自做火锅宴;或者就在科里宽敞的门厅里,举办联欢会,唱民族歌,跳新疆舞,自娱自乐;兴之所至,也会拉上一两个医生护士翩翩起舞,显出当年上海小帅哥的本性。呵呵! 他的夫人景用仪,大家闺秀,谙悉英文,因为嫁给他,辍学于教会学校大一。此后跟随他远来巴蜀,为人妻为人母,相濡以沫,不弃不离,后来在重医附一院病案科工作,直至退休。 尾声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的开头,回想董绍贤先生年5月离开洒满心血的重医时,从心底迸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重医,我的重医,我要走了!”在场的所有送行人或热泪盈眶,或掩面而泣。这是一位把毕生精力献给重医、献给麻醉事业的老人面对挚爱的一切,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有眷恋,有无奈,更有不舍。 我忽然想到董先生年秋日乘舟往巴蜀,吟苏轼诗抒怀的情景: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哀吾生之须臾。生命毕竟太短暂了。 年X月,董绍贤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至死,他的胸前还戴着科里同仁临别时赠送给他的平安玉佩;两年之后,夫人景用仪随他而去。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董景敏告诉我,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即患上脑出血,治疗后有好转,直至6年后仙逝。 年2月7日,渝中听风楼 赞赏 长按怎样治白癜风怎样治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