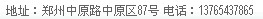|
最好的白癜风医院是哪个 http://pf.39.net/bdfyy/qsnbdf/140805/4440903.html 新冠病毒肆虐一年多,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乏趣甚至枯燥苦闷。令人称奇的是,另一种古老的病毒帮我打破了这种局面,只是其过程有一些悲喜剧的味道。 两周前的今天是清明节后的第一个周四,我照例不用上课。四月八号听起来是个吉利数字,天气特别好又暖和,实实在在的春暖花开。为了消除一年来的少乐气氛,特意去买了六支玫瑰三棵杜鹃,一共九种不同花色,兴冲冲地栽到院子里。忙活了三个多小时,虽然累得一身臭汗甚至手茧磨破,心情却是难得见好,还几乎耽误了下午四点的视频会议。急匆匆进屋,没顾得上冲洗便正襟安坐在屏幕前一个多小时。会议开得也蛮开心,看来差不多就要成就难得完美一天。可是,这波一动一静一热一冷的折腾是需要年龄底气的,不能逞强。 当晚不觉有事,睡的很好。第二天周五上课照样中气十足。到晚上开始就有受凉发烧症状了,期间还曾暗暗担心会不会新冠高戴。周六起出现质变,先是脸部开始不可描述的状况,接着是眼睛逐步变得有所事事。到周日,左眼针刺般疼痛,像是进了异物,用清水冲洗又毫无用处。紧接着是左边头部开始持续的神经性作痛,无法描述,难以忍受。要不是忌惮新冠,医院看急诊。 周一起来给家庭医生打电话,才知道我们原来的家庭医生搬走了,虽然有新的医生入驻接手,但家庭医生不看眼科疾病,要我找眼科专家(Ophthalmologist)。在美国找眼科医生要注意,如果搜索eyedoctor,出来的结果多半会是Optometrist(OD)或者是Optician。前者是有正规学历的验光师,后者是职业培训出来的配眼镜技师,两者都与看眼疾无关。我的运气不错,居然在第二通电话就找到一位眼科医生,当天下午四点过去就诊。这是一位看起来像印度裔的医生,网络评价很好,给人印象干练成熟亲和自信。医生的结论很快,是一种叫Shingles病毒作祟,也就是带状疱疹,是一种年长版的水痘。我其实更喜欢水痘这个名称,不像疱疹那样瘆人,听起来很嫩的样子。因为这个英文单词和德文的霉菌(Schimmel)容易混淆,为了避免弄错我请医生把这个单词写给我。他还特意标上更为准确的医学名词:herpeszosterophthalmicus。有了这些单词,通过谷歌和油管搜素,对这个病总算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实际上,在得过水痘或接种水痘疫苗后,这种病毒就会潜伏在身体里,等年龄增大免疫力下降时有可能再度复活。 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成人会得这种毛病,比例随年龄增长迅速提升。其实,是有疫苗可以防止这种病毒攻击,我以前没有留意过。不知什么原因,据说这种病在国内的发病率要低很多。国内好像没有自己开发的疫苗,但可以打一种来自英国的疫苗。需要自费,打两次要花人民币。说来惭愧,当下全球有超过一亿四千万人被新冠病毒追逐到,而我却有幸被在三百年前就确认的老病毒缠上,看来我这个人不是过于老派就是太无趣了。 对病情了解是一回事,该受的苦是照样逃不掉的。遵医就药后的前三天,情况还是继续恶化。电话询问得到的答案是,药效需要三天时间才出现。医生的话还得信,三天后果然开始慢慢好转,一周以后,持续的疼痛减弱了很多,甚至一度让人有已经康复的错觉,当然其中的反复是难免的。这个周一复诊结果是,眼部感染减弱但没有完全消除。医生估计还需要观察一个星期。不过,现在精神大致恢复,除了还有间隙性的头疼,没有其它太严重的症状了,估计一周以后应该可以继续上课了。只是脸上的痕迹,还在无脸见人阶段,确切地说是半无脸见人。这也是这个病毒的奇特之处---只害半边。所以,如果有人发现左右脸或者左右身体两边均有患处,说明所缠另有它毒。这是关于发病的故事。那休眠激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涉及到我医疗保险的特殊规定:在看专科医生之前,需要家庭医生开一份相当于介绍信的东西(Referral)。本来这也就是一通电话就能搞定的事,毫不夸张,我这次整整打了13次电话才解决。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我只在年刚刚找上这位家庭医生的时候做过一次常规体检,之后再也没有麻烦过她,算起来五年多了。有些时候,不麻烦别人是可能招惹麻烦。过往,诊所时不时给我发短信打电话,希望我定期去检查。而我一则怕烦,二来觉得没有必要,一直没去过。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把我列入了“休眠病人(inactivepatient)”名单。其实叫休眠病人是有点夸张的说法,真实的意思是不活跃病人。现在接手的这位家庭医生没有和我有过直接关联,因此,在请他们出具介绍信的时候,有些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我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要介绍信是中午1点刚过,接线员说1:30之前诊所接待室没人。一点半后,前后打了五次电话,诊所还是一直没人接电话,中间还有一次没有接通。出于无奈,我只好先通过语音留言请他们出介绍信。但是由于我的情况特殊,决定还是需要当面说清为好。到:10终于连线到了诊所接待室,提出了我的请求后,接待员要我等一下就没有动静了,中间居然延续三四分钟之久没反应。我只得挂掉重拨,如此这般前后四次。终于在第五次接通之后,才给我解释我是处在休眠状态,需要尽快预约一次去激活我的病人身份。还说,这次她们可以破例大度一次,先给我发推荐信,但是我得尽快去面见医生!这个时候,差不多到了下午三点了。说实在,这次打13通电话才办成一桩小事的经历,让我有点犹豫是否该换一家诊所了。公平地讲,在美国碰到这种极端例子的几率不大,特别是家庭医生诊所也需要维持稳定的病人资源才能运作正常。我估计,接待员当天可能出了什么状况,糟糕的心情碰上我这种不讨喜的病人,不小心就有点失控了。保险公司要求开介绍信的做法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不方便。我选的这类保险还有另外一个限制:除了急诊,只能在其涵盖的医疗网络体系内就医。但是这个网络足够大,除了有极端的需求,也不算是问题。而没有这两种限制的保险(PersonalChoice)可能需要多交两到四倍的保险费,觉得暂时不需要。有这种限制的医保名叫Keystone(拱石),这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保险品牌,而宾州由于其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而被称为拱石之州。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英文单词用德文发音听起来有点像“开始痛”。这次看病的小插曲激发了我对医疗保险的一些好奇,发现我们学校给员工提供的医保价格是不与工资收入挂钩的。而在欧洲,医保收费是工资的一个固定百分数,上有封顶。以00年德国为例,按年工资收入不超过5.8万欧元部分的14.6%收费,雇主雇员各一半。年工资5.8万欧元正好是德国所有工资收入的均值。这样算起来每月个人负担最多多欧元,涵盖全家。这与我们学校的医疗保险支出相当。但是因为与工资脱钩,在美国这意味着大家都需要承担这种最高额的保费。对于年资较高的人而言,这种负担与德国差不多,而对于收入偏低的员工而言,负担就要相对大的多了。这解释了两个有趣的现象:1.在德国,非法逃保现象出现在中等收入的个体营业人员较多(00年德国有14万人逃保,占总人口的0.%),因为他们需要全部自己缴纳全部14.6%的保险费。而在美国可能是较低收入者会没有医保(约1%的人口),因为保费相对比较贵。.美国人每年医疗相关支出约一万一千美元,接近同类发达国家平均值5千7百美元的一倍。如果上面所说的美国医保收费政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么这种差异正好对应了矩形和三角形面积对比的双倍关系。四月八日种下去的杜鹃已经开花了,而栽花的人却成了一个被动激活的病人还在等待完全康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该不该到家庭医生那里去正式激活我的病人身份并在此后继续保持一个活跃的状态。这听起来是一个小事,而背后的思想斗争则有点像法家与老庄的对立---该是依赖强化管理为好还是一切顺其自然更优?这是一个好玩的题目,我得好好想一想。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wkcme.com/mbywh/135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