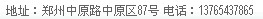|
“南极,我来了!” 潘曜,山西学子再次将自己名字写在了南极科考历史中。11月7日,随着汽笛响起,“雪龙”号破冰船驶离上海港口,他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之行(本报11月8日有过详细报道)。 整整一个月后,12月7日,本报记者在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窦银科教授的帮助下终于联系到了他。当地时间早晨6点多,记者将远隔万里之外的他从被窝中“拽”了起来,让他讲述出发之后的点点滴滴。 12月4日坐直升机到中山站“这里与国内有三个小时时差,现在我们这6点多,国内应该是9点多。”潘曜告诉记者,“雪龙”号在12月2日到达陆缘冰区开始破冰,4日晚上乘坐直升机到了中山站,目前任务很杂,当地时间早晨7点半,也就是国内上午10点出发去内陆出发基地集合开始一天工作,到了晚上9点,国内晚上十二点再回来。这几天任务是用装甲车把埋在雪里的雪橇拉出来,因为一年多没用,雪橇被埋在了雪里。潘曜他们主要是用钢丝绳把雪橇和装甲车连起来。“工作起来很费劲儿,体力消耗非常大。”能从这位经历南极科考选拔的人嘴里说出费劲儿,可见工作环境有多艰苦,有多累。 按照每次南极科考的工作流程,准备好雪橇之后,他们将开始卸载船上的货物,包括科考设备、日常保障物资等等,总重达几千吨,这又需要潘曜他们耗费更多体力和时间才能完成,接下来才能开始各自的科考任务,向南极内陆继续挺进。 一旦,潘曜向内陆进发,离开中山站,我们又要和他“失联”很长时间,为了完成采访,必须抓紧这段时间,而且只能利用他休息的间隙和他交流,不得不将他从睡梦中唤醒。 旅途大部分时间处于“瘫痪”状态回忆之前的旅行,潘曜说他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瘫痪”状态,本想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这次出行,但是什么都干不了,除了吐。这些“苦难”,师傅窦银科给他打过“预防针”,可是现实太骨感,一切都得自己来承受。参加过南极科考的人都知道,一般距离南极一个星期路程时候,船晃动非常剧烈。船上考察队员的状态大致有三类:一类是躺下起不来,不吃不喝型;另一类是吃饭时能起来,快速吃完即躺下型;第三类是不晕船、吃喝工作不误型。只有船员能是第三类人,而潘曜是第一类。身体躺在床上,没完没了地体验螺旋式失重与超重。吃饭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吃完不呕吐成为每个人心中的“期盼”。潘曜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老队员编写晕船十字歌内涵:一言不发,两眼发直,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卧不起,实在难受。 “不过,在船上队友之间很团结,相互照顾,这是我能坚持的动力源泉之一。”潘曜觉得,经历了晕船之后才能算真正成为了合格的科考队员了,不会忘记这次出行代表不仅仅是自己,身后有很多人都看着他,因此他每次被晕船折磨的时候,会多想想身后支持他、北京那个医院看白癜风哪家医院看白癜风便宜
|